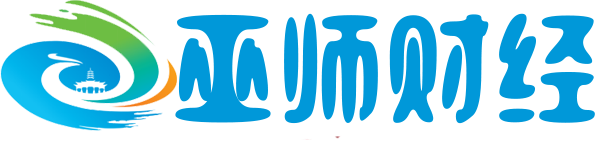风声|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的撕裂:只靠法律难以解决根本问题
 摘要:
作者|朱光星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近日,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二审维持原判的裁决,未能平息持续发酵的社会争议。甚至,即便审判...
摘要:
作者|朱光星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近日,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二审维持原判的裁决,未能平息持续发酵的社会争议。甚至,即便审判... 作者|朱光星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近日,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二审维持原判的裁决,未能平息持续发酵的社会争议。甚至,即便审判长答记者问中就几个关键问题进行了回应,仍未能止息社交媒体上的纷争。这起看似普通的刑事案件,因其特殊的案情背景而成为观察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裂痕的一扇窗口。
订婚强奸案判决引发了男女对立?
有人认为,这个案件使得“男女对立思维再度飙升”。但究其本质,这远非单纯的性别对立,而是不同文化价值观之间的正面交锋:
一方面,根植于父权制的传统性别文化在我国依然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受其影响在一部分人的观念中女性处于从属地位,他们将婚姻关系(甚至订婚)视为女性对性权利的让渡;另一方面,随着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性别平等理念的普及,一种强调个体自主、相互尊重的新型性伦理正在形成。
这种价值观念的代际更迭,必然会导致社会成员在爱情观、婚姻观和性观念上出现显著分化。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引发的舆论风暴,正是这种观念冲突的集中体现。
这种文化转型期的观念冲突并非中国独有,在西方性犯罪改革历程中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价值碰撞。以美国为例,在性同意认定标准这一构成强奸罪与否的核心议题上,美国社会中至少有“拒绝即同意”(No means Yes)、“拒绝即不同意”(No means No)和“肯定性同意”(Yes means Yes)这三种标准,分别代表了截然不同的认知观念和价值观取向:
“拒绝即同意”的传统观点认为,女性在性行为中的拒绝,可能只是“欲拒还迎”的表现,或者是一种调情的策略。这种观念根植于传统父权主义社会对性别角色的建构,实际上剥夺了女性的性自主权。
“拒绝即不同意”的标准是女性主义运动的重大成果,它承认女性说“不”就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要求男性必须尊重女方的明确拒绝,这一标准在20世纪后期西方国家的性犯罪改革中被广泛采纳。
更为激进的“肯定性同意”标准则要求性行为必须建立在持续、自愿、明确的同意基础上,不仅要求不存在对性行为的拒绝,还要求必须得有对性行为的肯定性同意。该标准体现了对性自主权更高程度的保护,但其制度设计也备受争议。
在美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掀起的强奸法改革浪潮中,各个州所采用的标准并非完全一致。其中,1988年宾夕法尼亚州的伯科威茨案,堪称最具争议性的司法判例之一。在本案中,就读于某大学的罗伯特伯科威茨被控强奸同校女生,根据法庭记录,在女生多次明确说“不”的情况下,伯科威茨仍执意与之发生性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受害者虽持续口头拒绝,但未进行肢体反抗,这一细节成为后续法律争议的焦点。伯科威茨承认受害女生当时有不断说“不”,但他认为这些“不”是夹杂在“情意绵绵……激情四射”的呻吟中发出的。他把女生的抗议视为一种微妙的鼓励行为,因而认为自己当时的性行为是获得了女生的同意和许可。对于该案,初审法院认定强奸罪成立,而上诉法院和州最高法院却以“缺乏物理强制力”为由推翻原判。
该案最终裁决公布后,立即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批评者认为,伯科威茨案中法庭的立场从某种程度上是将传统观念中认为的“女性在性行为中说‘不’只是一种‘象征性抵抗’而非真的拒绝”的理论通过司法实践予以认可。但也有人对该判决持支持立场,例如作家格雷格伊斯特布鲁克就曾公开为该判决辩护:“人类历史上半数的性行为——或许更多——始于女性最初说‘不’或多次拒绝。最终发展为双方自愿的性行为往往以女性说‘不’为开端。”
与之相反,1992年新泽西州的M.T.S案则确立了划时代的“肯定性同意”标准。该案中一名17岁的男孩与一名15岁的女孩进行了自愿的接吻和激烈的爱抚,随后男孩在女孩未同意的情况下与之发生了性行为。新泽西州最高法院在裁定意见中明确指出:“被告在未得到受害人对具体插入行为的肯定和自由许可的情况下,所实施的任何性插入行为都构成性攻击罪。”
美国强奸法改革浪潮中,关于“性同意”认定的标准之争,远非简单的法律技术之争,而是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性别关系本质的理解差异。
不分男女:另一种形式的“规训暴力”
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丹卡汉观察到了社会舆论在性同意这一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便设计了一项模拟陪审员实验——卡汉-伯科威茨实验,采用严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来探究文化价值观是如何影响人们对性侵案件的判断。
研究人员招募了1500名18岁以上的公民作为受试者,通过分层抽样确保样本在性别、种族、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等维度上都能准确反映美国人口的整体特征。研究团队将伯科威茨案做了匿名化处理和稍微改编后交给所有受试者阅读,该案件的事实部分明确记载了男女双方都承认的一个关键事实:女方在性行为前和性行为过程中多次明确说“不”。为了考察不同法律定义对人们判断的影响,研究团队将受试者随机分为五组,有四个组都收到了不同版本的强奸罪法律定义,还有一个组的成员没有收到任何法律定义。
在阅读完案件材料和相应法律定义后,所有受试者都需要就改编后的伯科威茨案中“女方是否存在有效同意”和“男方是否构成强奸”等关键问题作出判断。数据显示,受试者对性同意的判断呈现出鲜明的价值观分野:秉持平等主义世界观者更倾向于认定男方构成强奸,而持等级主义立场者则普遍认为性行为具有合意性。这种认知分化,还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案件事实的解读——即便面对“女方多次明确拒绝”这一无可争议的事实,等级主义者仍倾向于将其重构为“欲拒还迎”的暧昧表示。
这种认知差异的深层逻辑在于,等级主义者往往内化了传统的性别角色期待,将女性在性活动中的被动性视为道德纯洁的体现,因而将口头拒绝理解为“象征性抵抗”。在这种认知框架下,女性说“不”被理解为是男女性行为中的正常表现,而非女性的反对和抵制。平等主义者则认为对于女方在性行为中持续、明确的拒绝,男方应当予以重视和尊重,任何对“不”的重新诠释都是对女性性自主权的侵犯。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立并非简单的性别对立。卡汉的研究发现,最坚定地支持案中男方不构成强奸罪的人群,恰恰是持有等级观念的女性群体,特别是那些岁数较大的女性。
这些女性对受害者的苛责,某种程度上是另一种形式的“规训暴力”——通过谴责偏离传统等级主义性别规范的受害者,这些岁数较大的女性既维护了自己在等级秩序中的道德优越感,又强化了既有的性别权力结构。被父权制等级主义规训最深的女性,反而却成了该制度最顽固的维护者,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荒诞而又残酷的事实。
该研究还发现,在性侵案件的判断中,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往往凌驾于已有法律规定之上。数据显示,不同法律定义对实验参与者对案件最终判断的影响微乎其微,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们本来就有的内在文化认知。即使面对完全相同的案件事实和法律指引,持不同文化立场的人仍可能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这种判断的极化现象反映的,是更深层次的文化认知冲突。
单纯依靠法律,难以解决根本问题
卡汉实验中的文化认知理论,为我们解读山西大同强奸案的舆论撕裂提供了重要启示。
首先,大同强奸案中舆论场上的对立,绝非男女性别之间的对立。甚至,有不少男性对案中女方的强奸控告和二审法院的判决表示支持;当然,社交媒体上也不乏部分女性站在为男方开脱的阵营里。这种错综复杂的立场分布表明,我们面对的是一场关于法律应如何妥当规制男女性行为的文化价值观之争,而非简单的性别站队。
其次,单纯依靠法律修订,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虽然完善立法、明确司法标准至关重要,但若不能同步推动整个社会对强奸的文化认知变革,再完美的法律条文也很可能沦为社会偏见的注脚。
网上有个别法律从业者完全不谈案件事实本身,以赤裸裸的个人偏见对受害女性进行恶意揣测与攻讦,这提醒我们:
当面对诸如“性同意”这种具有社会敏感性的法律议题时,若法律人放任个人偏见遮蔽专业判断,不仅会动摇民众对其法律人“专业性”的信任,更会加剧社会的认知撕裂,法律人自身也会沦为文化偏见的共谋者。法治现代化,不仅需要制度完善,更要克服法律人自身的认知枷锁。
卡汉教授最终表示,美国国内关于强奸法改革的争议,本质上是不同文化群体间象征性地位的隐性博弈,要妥善解决强奸法改革争议,必须从根本上应对由于文化身份冲突引发的法律事实认知困境。
这一理论视角,同样适用于解读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判决后的激烈论争——表面上的法律争议,实则折射出更深层次的文化权力角逐。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战争中,每个群体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试图通过对“事实”的界定,来确认自身的社会地位和价值认同。
从伯科威茨案到大同案,历史不断重演着类似的认知冲突:当男性将女性视为欲望客体而非平等主体时,暴力便披上了“文化传统”的外衣。但现代法治的进步在于,它要求每个男性都认识到,对女性意志的尊重不是施舍的绅士风度,而是人格平等的必然要求;对女性身体的敬畏,不是虚伪的客套,而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底线。唯有将这一观念转化为全社会的文化共识,才能真正有效预防和减少性犯罪的发生。
“法治理想国”由中国政法大学教师陈碧、赵宏、李红勃、罗翔共同发起,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栏目。
主编 | 萧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