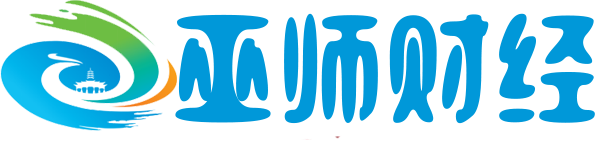学者马勇:现在制造出的大量论文垃圾,放到学术史上都没意义
 摘要:
学人简介:马勇,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兰州大学、河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主要从事近代中国文...
摘要:
学人简介:马勇,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兰州大学、河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主要从事近代中国文... 学人简介:马勇,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兰州大学、河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主要从事近代中国文化、中国近代史、中国文明史、中国学术史、儒学等方面的研究,著有《叠变》《中国儒学三千年》《晚清二十年》《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超越革命与改良》等书。
采访人:赵逸轩、陈诗浣,学人Scholar团队成员。本文标题为编者所拟。
01
我们这一代人,做学术就是偶然
学人:您生于1956年。与您同一代的前辈学者,大多经历过建国之初的动荡岁月,经历不同于后辈,走上学术研究之路,也多有机遇、偶然。请问,在您年轻的时候,是什么因素让您开启了作为学者的生涯?
马勇:你有个词语用得非常好,就是“偶然”,和你们不一样,我们做学术研究,真的是偶然的。我们在五十年代出生的人,还包括一些四十年代出生的人,年轻的时候都遇到了文革导致的停止高考招生。通常说“十年文革”,实际上高考停止了13年。等到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才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76到1977年,就有一群知识界做教育学的老先生,呼吁官方和社会,应该恢复高考。此前的高校主要是通过“工农兵”推荐来决定谁可以上大学,选出的学生的整体知识基础比较差,更多是凭借“政治表现好不好”,甚至“和部队有没有关系”来决定前途。可见,考试制度被废弃之后,整个选拔机制其实是很有问题的。因为我父亲在粮食站工作与大队书记、文教干事等人稍有交情。我大妹妹就作为工农兵,初中毕业就去上了大学。而我在部队当兵,举目无亲,我在1974,或者75年也曾被推荐上大学,经过了考试、面试诸环节,但最后还是没有去成,据一位朋友告诉我,被一个领导的孩子顶替了。从工农兵中选拔的学员大概从1972年到1976年招生了几届。
我到杭州警备区当兵,当时的目标就是提干、入党,之后就回家结婚。因为当时全国没有人口的流动,农村人连后来进城打工的机会都没有,如果不去当兵,就和祖祖辈辈一样,生生死死都在这个小地方。但是到1977年,我们当兵的就没希望了,因为不再从农村兵源中提干了。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人生节点。
同时,1977年,国家经济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变化,随着城市化、工业开发的规模剧增,全国出现了许多工厂,我从部队回来之后正好就赶上了农民工招工,我就算是中国的第一批农民工。我家乡在安徽淮北,所以就到了淮北煤矿挖掘队。煤矿被开采之前,就先由我们负责去打竖井、挖坑道。
图:1960到1970年代的淮北矿区
我在朱仙庄煤矿整整干了两年。那时国家刚刚恢复发展,百废待兴,需要大量技术人员,所以我当煤矿工的第二年,就通过考试考进了刚成立的淮北煤炭技术学校,属于正儿八经的中专。重回学校读书,让我们那一批从煤矿来的同学非常珍惜,好多同学相约在完成学业的同时,想方设法补习功课,争取参加全国高考,考上更好的大学。记得我那时和同学每周有几个晚上从宿县东关骑车进城参加补习,没日没夜补习一年,赶上了1979年高考,终于如愿以偿。
我本科上的是安徽大学历史系,我的高考分数里最低的数学只有13分。如果我能考63分的话,就可以直接上北大了。我能上大学是靠语文、历史和地理三门课。虽然我政治课一向也很好,但最后考了59分没及格。我英语是完全盲写的,全部选C。因为我年龄比较大,也没有任何准备,因为时代原因,我们这一代小学到中学其实就没学什么东西,到了高中毕业的年纪,几乎可以说是耽搁了十几年。
分数出来之后面临填报志愿。因为我数学、英语分数很低,总分也不高,所以不敢好高骛远,只是报了几个省内院校,专业课选的也就只有最传统的文史哲了,我就报了安徽大学历史系。
为什么选择历史而不是中文、哲学?因为此前不久的时候,全国范围内爆发了“批林批孔”运动,那时是1973到1974年。当时我正在当兵,也是高中生,因此连队读报纸差不多都是我来读。我当时迷迷糊糊,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东西,什么“焚书坑儒”,什么“秦始皇”,什么“儒家”,什么“法家”……我们中学没学过这些东西,所以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
图:1974年掀起的“批林批孔”运动席卷全国
因此到要上大学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要弄清楚这个问题,进了安徽大学历史系。我是1956年出生的,虽然不算班上年龄最大的学生,但也算岁数中等偏上的学生。最小的同学是62年的,最大的也有51年出生的。大学本科四年,最后半年我在考研究生,剩下的三年半当中,除了自己历史系的课,我还完整的去哲学系听了中国和西方哲学史的课程。因为我就是想要解决我之前的困惑——究竟中国的哲学史和思想史是什么样的?后来我就考研究生到复旦大学去了。我到复旦去,开阔了眼界。我选的专业就是专门史-中国文化史,真正进入到了这个领域当中去,也就是“入了门了”。
图:1980年的安徽大学,图片来自安徽大学官网
我研究生毕业时候,工作比现在好找得多,当时我就直接到了社科院来了。本来是要派遣去侯外庐先生的历史所思想史研究室,但后来给刘志琴老师将我换到了近代史所。刘老师是我的导师朱维铮先生的同学,她告诉我近代史所刚刚落成一幢宿舍楼和一栋办公楼,一进去,不用等,就能分到房子。那时没有后来的商品房,所有人都只能等着单位分房子。所以我毫不犹豫去了近代史所。因此我86年到北京来,88年我就有了一个20平米的平房。我在复旦学习的重点在中国古代史,毕业论文写的也是古代,汉代经学,只是那时比较宽松,我就进了社科院近代史所,然后慢慢就去做近代史。
到社科院来之前,我没有往近代史做过,因为当年和现在不一样,当年那些老先生给我们的感觉是“近代没有学问呐!”哪有什么“近代史”,就像今天有些人“觉得1949年之后哪还有历史?”一样。因此,当年我们读书的时候说“不读三代之下”,后来说“不读唐朝之下”。我在复旦的时候,一本本书的读下来,实际上读到唐朝,之后的作品就几乎没有了。虽然,我也跟着一个老师研究过一点明史,但更多的东西就不读了。主要就是当时的人认为,“越往后就越没学问,学问只在夏商周三代。最好的就是去学甲骨文,认识一个字,那就不得了。”但我是为了房子来了近代史所,近代史所的学问毕竟还是在近代,这样我就开始在近代史上下功夫。
从1986年开始,我一直读资料读到了1991年。几年的时间我没写过东西,就专门读近代史的资料。当时,“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是从1950年代开始出版的,我大概用了五六年时间,一本本的读书、借书,读书、借书…一直到1991年。
当时的学术风气,其实和现在很不一样。我们很幸运,所处的环境很好,老先生常说,不要急着写东西,要专心读书。所谓“读书”,就是踏踏实实地读一本书,把一本书拿来看、看进去。不像现在,好像连本科生都得写论文。其实我们当时是完全不写的,我一直到评中级职称时都没写过东西。评不上也无所谓,评上了写几句应付一下也行。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看重的是你有没有学问。几句话一听,老先生就能判断出来,“这个小伙子不错,有学问,表达得出来”,那就可以了。
我们真正得到的是什么?我算是下了功夫,花了大量时间在读史料上。后来也挺巧的,我原来做的是古代史,后来又转向近代史。这样一来,正好也契合了我们这行的一个理想,就是史学宗师司马迁说的“通古今之变”。如果说我的经验,那关键其实就是“歪打正着”。既研究古代,又研究近代;做近代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古代的那一套。现在偶尔我还在做古代方面的题目,偶尔也写写。
所以,我的学术道路也确实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我祖上没有人搞学问,我父亲只在私塾读过两年书,这跟学问毫无关系。我读本科的时候,他在家里让我读《论语》《孟子》,我朗读,他还会纠正我发音,说“这个字不是这样读的”,因为他跟私塾先生学的是古音——他知道这个不对,但我们家除了我父亲,没有人是搞学问的。所以我能走上这条路,说到底是偶然。但这一走,也真是不简单,这一走就是一辈子。
我一辈子除了干学术这件事,什么都没做过——没有当官,也没有经商。从1986年毕业,到现在,再加上之前七年的本科和研究生学习,我一直在这个领域里,一天也没离开过、也没转过行。
回头看,当年的确是阴差阳错才走到这一步。我后来招的学生里,也有跨专业的,比如有个学农的,是华中农大的。他来找我读博士,我说那你就做农学史的研究。后来我让他写《农学报》的研究,这份报纸是罗振玉编的,从1895年到1910年代。我通过关系在国家图书馆帮他弄了一张光盘,跟他说,你就一条一条地好好做出来。这种“学其他专业再来搞历史”,其实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假以时日,历史学的方法,总可以很好的融入其他的知识背景。
02
一路走来,我遇到了很好的时代和人
学人:在您漫长的学术人生中,哪些师友给了您比较大的影响和帮助呢?
马勇:那当然是有很多值得感恩的人。一路走来,真是感慨良多。大学阶段,尤其如此。
我本科是在安徽大学读的。这个学校到今天还是“211大学”,在安徽省内是重点高校,虽然在全国来说不算顶尖,但当时,我遇到的老师真的非常了不起。我是1979级,安徽大学历史系也就是那一年,我们这一届入学时建立起来的。老师们很多是从中学调上来的历史教师,有的是原来合肥教育学院的老师,文革时被下放,后来又重新请回来教书。
这些老师对我们管理非常严格,几乎是拿我们当中学生看待。每天晚自习都有人监督。我有时回想,觉得自己当了老师以后,根本没有像他们那样的耐心和投入。当年在那样一个并不特别突出的学校里,能有这样一群老师带着我们、管着我们,确实是非常幸运。
记得在读本科那四年,我在轻松而专注的状态下,把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典籍几乎都读了一遍。经史子,我那时从头开始,顺流而下,大致都浏览了一遍,这对于我后来的研究工作确实助益很大,使我知道遇到问题向哪儿找书。我后来一直告诉我的学生,书一定要诚实地读,不能寄希望百度寄希望于查找,看过和不看过完全不一样。
今天你们年轻一代面对的“商业机制”基本上是1992年以后才形成的,而在那之前,是没有这些压力和诱惑的。也就是说,当时读书就是读书,不为别的,只为自己学有所成。在安徽大学的那四年,正是这样的环境给了我潜心读书的机会。
后来考研究生,我的分数自然是很高的——否则复旦也不会要我。我记得是1983年去面试的。我是自己一个人跑到上海去的,那时我并不认识朱维铮老师。朱维铮当时只有四十几岁,在学界已经小有名气,但我并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谁是朱维铮,因为那时他也只是副教授,还不算特别有名。
图:朱维铮教授(1936-2012),江苏无锡人,德国汉堡大学荣誉博士,复旦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和史学史等领域研究。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面试那天他问了很多关于学术史的问题。我是从外地来的,身上没什么包袱,因此回答得很自然。他问什么我就讲什么,讲得兴致勃勃。讲到一半,他还得打断我:“好了好了,别说了。”——因为后面还有别的同学等着面试呢。如果不拦着我,我还能接着讲下去。
他问了哪些问题、提了哪些书,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也许是某本书,也许是某个历史人物。但当时我几乎每个问题都能对答如流,侃侃而谈。我们师生的感情很好。朱维铮老师的古代史、近代史研究很不得了。跟着他读书的三年对我的影响最大,我读了大概一年多的时候,别的同学说,“你和朱老师,现在连抽烟的姿势都一样!”但我其实并没想刻意模仿,这完全是潜移默化。在我的同学中,大概我的研究内容是最接近朱老师的,他做的内容,我大概都碰过,其中最难的像章太炎研究,这是朱老师的强项,我的同学没有人去碰,但《章太炎全集》是我参与整理的。
我50岁的时候因为生病需要戒烟,大概花了三年时间才把烟戒掉,那时戒烟必须靠意志,加上生病,我每天都头晕脑胀的,一点思路都没有。在这三年里,我没有写一篇文章,就读一点章太炎的资料,编了章太炎的书信集、演讲集。当时章太炎全集经过两三代学者的努力还没编完。清史委员会的朋友知道我在做章太炎的资料,就找到了我,问能不能把资料合到一起。后来又申请了一个章太炎全集的项目给了30万,有钱了就更好干了。后来又有出版社来问,能不能把你的老师、师祖编的《章太炎全集》给补完。现在的20卷本《章太炎全集》,前面的12卷是章门弟子、再传弟子、三传弟子几代人整理的,后面的8卷是我参与补齐的。在这个过程中,我真是下功夫读了章太炎的资料。后来我在其他很多方面受朱老师的影响也很大。
在我的学术进程中,受庞朴先生的影响也很大,他是《历史研究》的主编,几年前也去世了。庞先生研究的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中比较冷僻的学问,像火历、公孙龙的名学,清代学者方以智等。他在当年名气很大,文革后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给儒家平反。这是后来重新评价孔子、儒学的开篇。上海东方出版中心找到庞先生,想请他做一套四卷本的儒学的书,庞先生就找到了我。我又帮助找了几个师友一起完成。在那前后,庞先生参与主持的中国文化书院要为梁漱溟先生编一套全集,庞先生邀请我参与了其中一部分。我读梁漱溟的资料大概在毕业之后的第一年,应该得益于刘志琴老师的提醒,她和梁家有关系,他介绍我去梁家见过梁漱溟老先生。所以,庞先生领衔主编梁漱溟全集找到我,应该与此有关,由此又拓展了我的视野。
编完之后当然要写了,到现在为止,我应该已经写了五六遍梁漱溟了,但每次写并不是抄自己,而是有新资料或新思考了,去重新写。
图:庞朴教授(1928-2015),江苏淮阴人,山东大学终身教授,曾任《历史研究》主编。是中国思想史、儒家研究和出土简帛研究等领域的权威。
还有我们的老所长王庆成先生。王先生注意到我,是因为看到了一篇我写严复的小文章。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5卷本的《严复集》,30多块钱,当时我们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过300块钱,我就咬着牙把这套书买下来了。买下来之后的目标,当然是要把这个钱赚回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投给了《文史知识》,《文史知识》把它给发了,这样第一笔稿费就把这个钱弥补回来了。那篇文章今天看是不成样子的,我看到都会觉得很尴尬。当时所长王庆成刚好看到了我这篇短文,他当时跟严复的后人有一个合作项目,就问我愿不愿意干,我当然愿意干了。大概1987-1988年,我就帮着王先生整理严复的资料。后来,我就研究严复到了现在,今年才刚刚把我写的严复传重新改了一遍。可以说,如果没有王先生对我的肯定,我可能写一篇文章把书钱挣回来就拉倒了,不可能持续地做严复的研究。这几十年来国内外开研究严复的会还没有漏掉我的,因为我在这一块儿还算持续坚持的一个学者。所以我很感激王先生。
图:王庆成教授(1928-2018),浙江嵊县人,近代史学家,曾任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精于太平天国史研究。
刘大年先生是近代史所的名誉所长,年轻时是做经学史研究的。我来近代史所后,他或许看了,或许听说我的毕业论文,写汉代经学的,据一位经历此事的老先生后来告诉我,大年先生想让我帮他整理近代经学方面的资料,一起做这方面的研究。可能是当时中间传话的人没讲明白,或者因为其他原因,这件事情没有变成现实。但到了1990年代初,抗战研究刚刚启动,在这之前抗战作为一个政治话题,并没有真正进入研究环节的。这时为了给1995年的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做准备,刘大年等一批参加过抗战的老先生出面组织学会,创办刊物,组织丛书,其中就有大年先生主编的一部抗战史上马。我和所里一批年轻学者一起参与,丁守和等老先生审读、顾问,这就是1997年出版《中国复兴枢纽》。这部书现在应该也成为名著了,翻译成了好几种外语。由于当时宽松的学术环境,里面的许多论述具有开拓性,当时我负责的是抗战时期的中国思想文化。
图:刘大年教授(1915-1999),湖南华容人,近代史学家,曾任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刘先生在抗战时期冀西、冀南抗日根据地成为一名战士,建国后作为抗战史学家工作
刘大年找我谈话一开始就说,他虽然经历了抗日战争,但对这个时期的思想文化也没有研究过,也不懂,让我按照自己的阅读理解随便写。我被他这一忽悠,一下子写了20多万字。稿子交给他之后,大概一个月他看完,说找我来谈谈,他那时大概快80岁了吧,他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干,能不能这样改一下,提出了几个问题,我很佩服他,就按照那个思路改了下;后来他说控制在6万字还是多少,最后就改出来现在这本书。在国内外对抗战思想文化的研究中,在这之前国内外学术界,包括台湾、美国,都没有把抗战时期中国思想文化发展脉络勾画出来,讲出个整体,可能有对个别人物的研究,但都没有涉及对中国思想文化脉络的研究。我在这本书里应该算第一次把这个课题做明白了,讲清了抗战时期各个思想流派的发生演变及其主旨。后来所里组织的《中国近代通史》,仍然把我写的这一部分完整吸收了。
我也很感谢老院长汝信先生,大概在1990年代亨廷顿讲文明的冲突之后,中央要求研究一下文明究竟是不是个问题。我们院就成立了一个跨学科的课题组,联合了18个研究所,参加的人员中我年纪最小,其他人都是老先生。后来我写了六七十万字,形成了《中国文明通论》这本书。
图:汝信教授,出生于1931年,江苏吴江人。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哲学研究所所长。曾师从贺麟学习黑格尔哲学,关注美学领域研究。
这一辈子走到现在,我觉得主要还是我运气比较好,能遇到师友的赏识,给我提供帮助和机会,让我的研究面比较广。如果没有那些偶然的机会,我怎么会下功夫研究严复,研究中国文明呢?但是,参加这些项目,一个题目要做好几年,有时候也确实会耽误自己的事情,比如我其实一直想写一本经学史。但我觉得,还是很感恩这个时代,感恩遇到的这些老师,遇到的出版社编辑和媒体。我是属于比较温和的人,比较好合作。我毕业之后大概三年就出书了,当时我只是个一文不名的年轻人,四川人民出版社就给我出书了;过了两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一年给我出了两本书。我觉得我遇到了很好的时代和一批真正热心学术的出版人。有的老先生、老编辑不在了,但我确实经常会想起他们对我的关怀、教育。
03
创新要立足于踏踏实实的阅读和思考,没有办法偷懒
学人: 您做了很多涉及不同领域的研究,像抗战思想和严复研究。涉及一个很大的历史题目时,可能需要跑到世界不同地方找资料。您怎么看自己找资料的这段历程,有什么可以分享的体会?
马勇: 所有的历史研究都要从资料开始。我读研究生时选题目也讨论了很久,一开始是研究汉代经学,最后慢慢规划为汉代春秋学。老师就指点我去外面找资料,上海图书馆,复旦图书馆,师大图书馆等,去那里翻看目录卡片,找和自己研究相关的东西。因为1980年代,国内电脑远远没有普及,没有任何网络搜索工具。后来到了北京,没课的时候,我就对研究所的图书做了全面的“普查”,把卡片盒子拉出来一页页翻看,看可能有什么东西和我要做的研究有关。然后再到隔壁的科学院图书馆去翻,再是国家图书馆,那时叫北京图书馆,离我们很近,骑个车子就过去了;再就是首都图书馆,那时好像在国子监,我从这些公共图书馆获益无穷。
图:文史工作者用以记录和归档材料的“小卡片”(左),以及存放小卡片的箱子(右)
我就在北京这个范围内,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人民大学图书馆、清华博物馆……北师大图书馆去普查,普查做完之后需要做项目的时候,就知道怎么找资料,就会想到之前好像在北师大看过这个东西。
那时候还没有检索目录,我们当年是这样来扩充自己的资料。后来慢慢的印刷品也多了,印刷品真正变多,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之后。改革开放之前,像国家图书馆的藏书都是49年之前的,49年以后到改革开放这段时间没书,完全没有出版物。将来去研究的时候会很困难,因为没东西。
当时的学者都在写检讨,写批判文章,有的要批判胡适了,写几篇文章,最后结成个集子,这段时间是空档。等后来我们进入研究了,新书开始出来了。新书出来之后,我每个星期或者每个月会骑自行车到琉璃厂去,总会带回来一批书。我大概有十年时间到那儿买了好多书,后来等潘家园起来,再到潘家园去淘旧书。后来慢慢的,主题就比较明白了。找资料是历史学的基本功,就是傅斯年讲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历史学就是靠资料说话的,资料是第一位的。
现在当然就简单多了,你们这一代有大量的数据库,大量的检索工具,跟我们当年不一样。但是我对我的学生,我都要求他们要去读。对我们的年轻朋友讲,如果不去读,就指望着百度、谷歌是没办法建立体系的。你的体系来源于你的阅读。学问的最后是看你在这一代又一代的学问基础上,能够讲出什么新意来。没有整体性的贡献,那就很难,而这就立足于一本本的书。我当年不是为了做题目去找资料,而是读到足够多的时候,题目会油然而生。我是从先秦顺流而下,一路读下来的。在我的作品目录当中,可以看到古代中国的、近代的、现代的都有。实际上一篇论文如果没有新意,我就不会强制去写了。我读公孙弘,觉得有点新意,写公孙弘那篇文章有一万多字吧,我也是一个星期就完成了。因为把资料读熟了,脑子里就建立一个问题意识,我要讲公孙弘,要讲一个什么问题,解构他的话就很容易了。所以,年轻的朋友还是要把重心放在读书、读资料上,在这儿下功夫,厚积薄发。
现在是一个功利社会,可能大家就无所谓,有个题目就做,实际上一个题目做完就结束了。你只有像我这种做法——在大量的阅读之后,而且系统挖的越多,你就有做不完的题目。这也谈不上经验,因为老一代都这样做,老一代人都知道,要把工具准备好。就拿中国史来说,无论做哪一段,工具要准备好,古汉语一定要过关。即便做近代史,古汉语也非常重要,越到近代的古文越难读。当代的钱钟书的古文字比理解汉唐要难得多,因为他刻意用典,还不如读《史记》、《汉书》,它们的典故少,越往近代用典越多。为了理解典故,我们会费很大的功夫,总体来讲也没什么捷径,真不是靠检索就能够构成文章的。
另外更不要用AI。一开始我的学生跟我讨论过,要用AI,但最后你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你写的还是它写的,久而久之你就被它讲迷糊了,就不好了。我一直到现在对AI都是很谨慎的,我会在上面问一下,但是我绝对不把结果复制到我的文章当中去。一定要写自己的完整的表达,AI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但是参考完就pass掉,不要去积累它。人文科学是一个非常独创性的学科,想到哪个地方就写到哪个地方,这才是独创性。人文科学讲求创新,不然学问就没意义了。现在制造出的大量的论文垃圾放到学术史上都没意义,评学位、评职称可能有用。但是人类最后是在学术史上进行检讨,再过50年、500年的时候,我们的研究,我们的论文,还有没有后续研究者提及,这才是重要的,尽管研究者本人可能不知道了。但这才是历史,这就是历史学的贡献。如果你讲了之后,过了20年,完全从学术上消失,或者整个胡说八道,没意义,那就失败了。所以学术研究没有办法偷懒。它的创新就立足于踏踏实实的阅读和思考。
学人: 学人之前也访谈过人工智能方面的教授学者,提到人文学科确实不能依靠AI,因为这是一个独立的知识门类。而我自己的体会是,用AI有让人不放心的地方,有些史料居然是它自己生成的。
马勇: 这个最可怕,你根本没法验证,它编的很像,但是这个东西就是真真假假的,我想就是不能用。上次北京电视台找我做节目的时候,我提出这样一个自动化的东西,可能反而让纸质书更有意义。总觉得我得还原到纸质书上,哪怕我是找PDF电子版,我也得还原到这上面去。因为你们现在刚刚起步,开始在这点上一定要建立很好的规则,否则你就弄不明白了。
我们讲一个小八卦:当代一位著名学者批评另一位著名学者的代表作有抄袭,因为是公开批评,我就找来看了。我看了之后,我认为就是当年不规范的情况下,被批评者稀里糊涂的可能是抄了研究先进的话,但过了一段时间抄者忘记了,就觉得自己也是这种表达,就被批评者揭发了,就引起了巨大的舆论风波。因此从一开始就要养成良好的习惯。
学人:也可能是因为别的学科没有历史学很早就这么重视注释?
马勇:中文系不像历史那么严格。历史写作,我多年写作就是分成不同层次的。给大众看的,太过引经据典也不对。引经据典给大众看的话,就等于在折磨人,就把你的读者也给消灭掉了,是不对的,实际上学问是分成几个层面的。换言之,学术是一个良心活,不论你引证多寡,注释多少,都必须是自己的研究,但同时要注意自己预设的读者对象。写给大众的,就要让大众看懂,喜欢阅读,否则就没有意义。更专业的研究,本来就没有考虑读者,就是为了弄清问题,那么就应该广证博引,收集更齐全更完整的证据,不厌其烦,不厌其多。